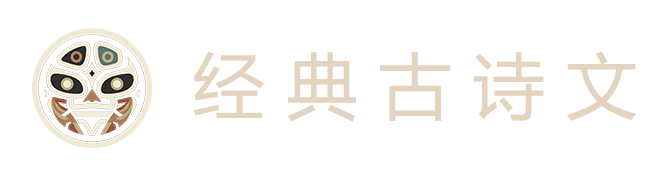人物生平
家族背景
元稹(779年-831年),字微之,别字威明,唐河南府东都洛阳(今河南洛阳)人,父元宽,母郑氏,为北魏宗室鲜卑族拓跋部后裔,是什翼犍之十四世孙。元稹家族久居东都洛阳世代为官,五代祖元弘,官至隋北平太守,四代祖元义端,官至唐魏州刺史,曾祖元延景,为歧州参军,祖父元悱官至南顿县丞,父亲元宽任比部郎中、舒王府长史。
早年经历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二月,元稹出生于东都洛阳城南,八岁那年父亲元宽因病去世,出生书香门第的母亲郑氏,用柔弱的肩膀担起了元稹上学的担子。天资聪颖的元稹不负母亲厚望,15岁参加朝廷举办的“礼记、尚书”考试,实现两经擢第;23岁登吏部科,授校书郎;28岁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授左拾遗,职位为从8品。早年元稹和白居易共同提倡“新乐府运动”,后人把他和白居易并称“元白”。
初进宦海
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十五岁的元稹以明两经擢第。唐代科举名目甚多,而报考最多的科目则为进士和明经两科。不过两科相比也有难易之分,进士科难,“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科“倍之,得第者使一二”,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而唐代文人也更为看重进士科。元稹为尽快摆脱贫困,获取功名,选择投考的为相对容易的明经科,一战告捷。及第之初的元稹却一直无官,闲居于京城。但他没有终止勤奋学习。家庭藏书给他提供了博览群书的条件,京城的文化环境和他的广泛兴趣,陶冶了他的文化修养。次年得陈子昂《感遇》诗及杜甫诗数百首悉心读之,始大量作诗。
贞元十五年(799年),二十一岁的元稹寓居蒲州,初仕于河中府。此时,正当驻军骚乱,蒲州不宁。元稹借助友人之力保护处于危难之中的远亲。乱定,与其家少女相爱。不久,元稹牵于功名,西归京城应制科试。
选婚高门
贞元十八年(802年)冬,元稹再次参加吏部试。次年春,中书判拔萃科第四等,授秘书省校书郎。贞元十九年(803年),二十四岁的元稹与大他八岁的白居易同登书判拔萃科,并入秘书省任校书郎,从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好友。元稹出身中小地主,门第不高,只有入仕以后,才有结婚高门的资本,如今作了校书郎,这时,元稹正值风华正茂,才华横溢,自然就把终身大事提上了日程。据韩愈《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墓志铭》云:“选婿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祺时始以选校书秘书省中”,元稹授校书郎后不久便娶韦夏卿之女韦丛为妻。十月,岳父韦夏卿授东都洛阳留守,赴东都洛阳上任,由于韦丛是”谢公最小偏怜女”,割舍不下,于是元稹、韦丛夫妇一同侍从韦夏卿赴洛阳,元稹夫妇就住在东都洛阳履信坊韦宅。元稹次年初才返回京城,而依据元稹诗文韦从则久居洛阳,这一阶段元稹因家事多次往返于京城与洛阳。
一贬江陵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四月,元稹和白居易同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白同及第,登第者十八人,元稹为第一名,授左拾遗。元稹一到职立刻接二连三地上疏献表,先论“教本”(重视给皇子选择保傅),再论“谏职”、“迁庙”,一直论到西北边事这样的大政,同时旗帜鲜明地支持裴度(时任监察御史)对朝中权幸的抨击,从而引起了宪宗的注意,很快受到召见。元稹奉职勤恳,本应受到鼓励,可是因为锋芒太露,触犯权贵,反而引起了宰臣的不满,九月贬为河南县尉。白居易罢校书郎,亦出为县尉。此时,母亲去世,元稹悲痛不已,在家守孝三年。此后,三十一岁的元稹被提拔为监察御史。
元和四年春(809年),奉命出使剑南东川。初登官场,意气风发,一心为民,报效国家,遂大胆劾奏不法官吏,平反许多冤案,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和崇高赞誉。白居易更是作诗赠他“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东川八十家,冤愤一言申”。这一举动触犯了朝中旧官僚阶层及藩镇集团的利益,很快他们就找了机会将元稹外遣——分务东台。东台就是东都洛阳的御史台,用意在于将他排挤闲置。即便遭受到这样的打压,元稹仍然坚持为官之初的原则,秉公执法。同年,正值仕途受挫时,其娴淑聪慧的妻子韦丛盛年而逝,韦丛之死,对元稹打击很大,使他常常夜不能寐。由于难遣伤痛,元稹写下了有名的悼亡诗——《遣悲怀三首》。
元和五年(810年),元稹因弹奏河南尹房式(开国重臣房玄龄之后)不法事,被召回罚俸。途经华州敷水驿便宿于驿馆上厅,恰逢宦官仇士良、刘士元等人在此,也要争住在上厅,元稹据理力争,却遭到仇士良的漫骂,刘士元更是上前用马鞭抽打元稹,打得他鲜血直流,最终被赶出了上厅。后来唐宪宗便以“元稹轻树威,失宪臣体”为由,贬元稹为江陵府士曹参军。从此开始了他困顿州郡十余年的贬谪生活。
二贬通州
元稹因才华出众、性格豪爽不为朝廷所容,流放荆蛮近十年。随即白居易也贬为江州司马,元稹量移通州司马。虽然通州、江州天远地隔,可两人来往赠答,计所做诗,有自三十韵、五十韵直至百韵者。江南人士,驿舍道途讽诵,一直流传至宫中,里巷之人互相传诵,致使市上纸贵。由诗中可知其流离放逐之心境,无不凄惋。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三十七岁的元稹一度奉诏回朝,以为起用有望。途经蓝桥驿曾题诗留赠命运相似的友人刘禹锡、柳宗元。抵京后,与白居易诗酒唱和,意气风发。元稹收集诗友作品,拟编为《元白还往诗集》,但书稿未成,却突然与刘禹锡、柳宗元一同被放逐远州。元和十年(815年)三月,元稹“一身骑马向通州”,出任通州司马。流落“哭鸟昼飞人少见,怅魂夜啸虎行多”(《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的通州,他“垂死老病”,患上疟疾,几乎死去。曾赴山南西道兴元府求医。潦倒困苦中,诗人只能以诗述怀,以友情相互慰藉。在通州完成了他最具影响力的乐府诗歌《连昌宫词》和与白居易酬唱之作180余首。
三贬同州
随着平淮西后的大赦和元稹知己旧识崔群、李夷简、裴度相继为相,逐渐改变了他在政治上长期受压抑的处境。元稹于元和十三年(818年)已代理通州刺史,岁末,转虢州长史。元和十四年冬(819年),唐宪宗召元稹回京,授膳部员外郎。宰相令狐楚对其诗文深为赞赏,“以为今代之鲍、谢也”。
元和十五年(820年),唐穆宗及位后,因宰相段文昌之荐,元稹授祠部郎中、知制诰。唐穆宗为太子时已喜爱元稹诗歌,此时特别器重于他,经常召见,语及兵赋及西北边事,令其筹画。数月后,被擢为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与已在翰林院的李德裕、李绅俱以学识才艺闻名,时称“三俊”(《旧唐书·李绅传》)。在迅速升迁的同时,元稹陷入了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漩涡,与李宗闵的积怨爆发,埋下党争的种子。不久,由于误会等原因,裴度弹劾元稹结交魏宏简,元稹被罢承旨学士,官工部侍郎。次年春,元稹、裴度先后为相。在唐王朝与地方军阀的斗争中,元稹积极平息骚乱,拟用反间计平叛。可觊觎宰相之位的李逢吉与宦官勾结,派人阴谋诬告元稹谋刺裴度,后虽查清真相,但元、裴被同时罢相。元稹出为同州刺史。
长庆三年(823年),他被调任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唐敬宗宝力元年(825年),元稹命所属七州筑陂塘,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在浙东的六年,元稹颇有政绩,深得百姓拥戴。
四贬武昌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九月,元稹入朝为尚书左丞。身居要职,有了兴利除弊的条件,他又恢复了为谏官时之锐气,决心整顿政府官员,肃清吏治,将郎官中颇遭公众舆论指责的七人贬谪出京。然而因元稹素无操行,人心不服。时值宰相王播突然去世,李宗闵正再度当权,元稹又受到排挤。大和四年(830年)正月,元稹被迫出为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军节度使。大和五年(831年)七月二十二日暴病,一日后便在镇署去世,时年五十三,死后追赠尚书右仆射,白居易为其撰写了墓志。
参考资料:完善
1、《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一十六》2、《新唐书·列传第九十九》3、《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一十六》4、《新唐书》参考资料
1、《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一十六》2、《新唐书·列传第九十九》3、《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一十六》4、《新唐书》
主要影响
文学
诗歌
元稹在诗歌、小说、散文、文学批评等方面都卓有成就,而以诗歌成就最突出。他与白居易发起了诗歌运动——新乐府诗歌,由元稹开先河、白居易参与完备、流传千年的诗歌派别——元和体(唐宪宗元和年间,元稹、白居易俩人所写的、注重诗歌语言平易浅切和通俗性的长篇排律)不仅“诗到元和体变新”,且天下文人“递相仿效,竟作新词”。
元稹所在的元和诗坛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是唐音渐趋宋调的转型时期。元稹作为这次新变中的具有不可替代意义的重要诗人之一,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据显著的一席。
元稹的诗学主张及理论批评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乐府古题序》《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序》《叙诗寄乐天书》《上令相公诗启》《杜君墓志铭》《白氏长庆集序》等作品里。在《乐府古题序》中,元稹条述了诗史的源流正变,反对“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主张“寓意古题,刺美见事”,推崇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诗篇,“即事名篇,无复依傍”,赞美了杜甫的新式乐府创作。“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八字极好地概括了新题乐府的特色,也肯定了“寓意古题,刺美见事”。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里,肯定了李绅《乐府新题》“雅有所谓,不虚为文”,这与白居易在《新乐府序》里所倡导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的精神完全一致,对于新乐府的创作实践颇具有纲领性意义。
乐府诗在元诗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启发了创作新乐府,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缺点是主题不够集中,形象不够鲜明。和刘猛、李余《古乐府诗》的古题乐府19首,则能借古题而创新词新义,主题深刻,描写集中,表现有力。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在元集中也列为乐府类,旨含讽谕。元稹非常推崇杜诗,其诗学杜而能变杜,并于平浅明快中呈现丽绝华美,色彩浓烈,铺叙曲折,细节刻画真切动人。元诗中最具特色的是艳诗和悼亡诗。他擅写男女爱情,描述细致生动,不同一般艳诗的泛描。悼亡诗为纪念其妻韦丛而作,《遣悲怀三首》流传最广,,它表达对亡妻的不尽思念,写得悲气袭人,令人不由得一掬同情之泪,其中第二首的结句“贫贱夫妻百事哀”为世所熟诵。还有《离思五首》(其四)也极负盛名。此诗写久藏心底的不尽情思,因为与情人的曾经相识而自此对其他的女人再也不屑一顾(“取次花丛懒回顾”),诗中的比兴之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语言幻美,意境朦胧,十分脍炙人口。
在诗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韵相酬”的创始者。《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均依次重用白诗原韵,韵同而意殊。这种“次韵相酬”的做法,在当时影响很大,也很容易产生流弊。元稹曾自编其诗集、文集、与友人合集多种。其本集《元氏长庆集》收录诗赋、诏册、铭谏、论议等共一百卷。
元稹诗歌在语言艺术上的成就是用语浅近。与崇尚奇险的韩孟诗派不同的是,元稹善于用浅近平易的语言准确传神地表情达物,直抒胸臆。浅近是元白诗派的最大特点,也是它获得广大读者的重要原因。在诗歌学中,常语和奇语是一对值得重视的矛盾。从表层意义上看,似乎以常语入诗比务奇斗险要容易得多,但如果从更高的审美层次来审视,用浅近的语言确切精细地摩写出自然界万物情状以及诗人自己的心态,倒是一种较难达到的艺术境界。元诗的喜用常语,在明白晓畅的乐府诗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在写景抒情诗中表现得也很突出。诗人对大自然怀有浓厚炽烈的兴趣,自然万物的一举一动都强烈地奉动着诗人的诗思,被他迅速及时地捕捉到诗思。元稹与刘宋诗人谢灵运不同,他重神似而不重形似,以浅显语言贴切自如地传达出风光物态,如《红芍药》。语近的特点不仅出现在元稹的咏物诗中,也出现在他的悼亡诗中,如《遣悲怀三首》。元稹的常语并非率尔为之,相反,他非常注意选语的精工。清人贺裳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诗至元白,实一大变。两人虽并称,亦各有不同,选语之工,白不如元;波澜之阔,元不如白。”元稹运斤成风,既苦心经营又不露斧凿痕迹,如《李娃行》。元稹在追求语近的同时,也把思深作为自己诗歌的创作目标。在一些抒情诗中,元稹做到了语近和思深的有机统一,如《梦井》。
元稹与白居易齐名,同为“新乐府运动”的领导者、“元和体”的首倡者,世称“元白”,在唐诗史上两人如双峰特起,论唐诗者辄曰前有李杜,后有元白,前后辉映,成为中国诗史的巍巍丰碑。元白堪称元和长庆诗坛的旗手,不仅以其创作产生广泛影响,而且以理论相鼓吹。贺裳称元白论诗“深得六艺之解”(《载酒园诗话》卷三)。
古文
元稹是中唐“古文运动”的首倡者和领导者,在散文方面也有一定成就。在元稹传世的散文中,制诰数量最多,占一半以上,成就也最高。立论纯正,举事周详,旨趣明确,措词雅驯是元稹制诰文的总体风貌,它一改先前制敕堆砌典故、四六套话、头肩腹腰尾干篇一律的陈腐面孔,有如春风吹拂大地。《唐书》本传载:“辞诰所出,然与古为侔,遂盛传于代。”这种英姿勃发的新体圣旨受到朝野一致欢迎是情理中事。因为它重塑了皇帝和最高领导机构的形象,使本来并不英明的穆宗皇帝变得胸有全局、知人善任、通情达理,且不失幽默感;同时也显得政令畅通,国家机器运转正常而有效。在国家多事之秋,能有这样一线亮光温暖人心弥足珍贵。唐穆宗高兴地说:元稹的革新制诏,“使吾文章语言与三代同风”。他以古文制诰,格高词美,为人效仿。
在创作实践上,元稹诗文兼擅,《元稹集》存文三十多卷,诸体该备,时有佳作名篇。
传奇
元稹创作的传奇《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叙述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悲剧故事,文笔优美,刻画细致,为唐人传奇中之名篇。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艳诗及悼亡诗》附《读〈莺莺传〉》中指出:“《莺莺传》为微之自叙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固无可疑。”后世戏曲作者以其故事人物创作出许多戏曲,如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和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等。
政治
整顿法度
元稹在朝廷任监察御史时,在整顿法度方面做出了不小的成绩。元和四年(809年)朝廷派他担任剑南东川(相当于今天的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一带)详覆使,前往东川调查泸州小吏任敬仲的贪污案,顺便调研采访,看看有没有其它不法事件。元稹到了泸州开始着手调查,发现在任敬仲的事件中牵涉到泸州刺史刘文翼的贪污行贿案,刘文翼的贪污行贿又和前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随着调查的深入,元稹发现严砺犯有收受贿赂、诬陷良民、擅自没收百姓财产、擅自征收赋税留为己用等不法行为。元稹把这些写成长篇弹状上奏朝廷,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和崇高赞誉。白居易更是作诗赠他“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东川八十家,冤愤一言申”。
元稹完成出使任务,回到朝廷之后,继续充满激情地履行着自己作为御史的职责,在几个月内又先后调查并上报了十余起违法案件,弹劾的人员包括浙西节度使、河南尹、武宁王等高官贵戚。后来元稹担任尚书左丞,出任郎官,与违法乱纪的七个朝臣交锋争斗,在整顿法度,肃清吏治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
地方政绩
元稹在地方做官时也作出了显著的政绩。元稹在通州,前三年任司马,后担任代理刺史七个月。他整顿吏治,出台政策,“赏信罚必,市无欺夺,吏不侵轶”。他引导百姓除草开荒,着手改变通州的落后面貌;还在南外翠屏山建戛云亭居宿,亲事农事,指挥农业生产;同时亲拟祝文三篇,在华阳观祭天气,求上苍风调雨顺、来年丰收、百姓安康。因为元稹情系百姓,政绩累累,当年通州人在他离任时登高而望,目送天涯,留下了“元九登高节”这一民俗。
元稹在武昌时,关心修水利以发展农业,均贫富以定税籍等改善百姓生活的事情。在岳州大水灾期间,元稹察知辖地实情,上奏朝廷,开仓出官米赈灾,救护百姓。后又向朝廷请求捐免当地秋租,解决百姓生活困难。
元稹的诗词作品
-
《酬乐天吟张员外诗见寄因思上京每与乐天…咏张新诗》
乐天书内重封到,居敬堂前共读时。四友一为泉路客,
三人两咏浙江诗。别无远近皆难见,老减心情自各知。
杯酒与他年少隔,不相酬赠欲何之。 -
《别后西陵晚眺》
晚日未抛诗笔砚,夕阳空望郡楼台。
与君后会知何日,不似潮头暮却回。 -
《望云骓马歌》
忆昔先皇幸蜀时,八马入谷七马疲。肉绽筋挛四蹄脱,
七马死尽无马骑。天子蒙尘天雨泣,巉岩道路淋漓湿。
峥嵘白草眇难期,謥洞黄泉安可入。朱泚围兵抽未尽,
怀光寇骑追行及。嫔娥相顾倚树啼,鹓鹭无声仰天立。
圉人初进望云骓,彩色憔悴众马欺。上前喷吼如有意,
耳尖卓立节踠奇。君王试遣回胸臆,撮骨锯牙骈两肋。
蹄悬四跼脑颗方,胯耸三山尾株直。圉人畏诮仍相惑,
此马无良空有力。频频啮掣辔难施,往往跳趫鞍不得。
色沮声悲仰天诉,天不遣言君未识。亚身受取白玉羁,
开口衔将紫金勒。君王自此方敢骑,似遇良臣久凄恻。
龙腾鱼鳖啅然惊,骥肦驴骡少颜色。七圣心迷运方厄,
五丁力尽路犹窄。橐它山上斧刃堆,望秦岭下锥头石。
五六百里真符县,八十四盘青山驿。掣开流电有辉光,
突过浮云无朕迹。地平险尽施黄屋,九九属车十二纛。
齐映前导引骓头,严震迎号抱骓足。路旁垂白天宝民,
望骓礼拜见骓哭。皆言玄宗当时无此马,不免骑骡来幸蜀。
雄雄猛将李令公,收城杀贼豺狼空。天旋地转日再中,
天子却坐明光宫。朝廷无事忘征战,校猎朝回暮球宴。
御马齐登拟用槽,君王自试宣徽殿。圉人还进望云骓,
性强步阔无方便。分騣摆杖头太高,擘肘回头项难转。
人人共恶难回跋,潜遣飞龙减刍秣。银鞍绣韂不复施,
空尽天年御槽活。当时邹谚已有言,莫倚功高浪开阔。
登山纵似望云骓,平地须饶红叱拨。长安三月花垂草,
果下翩翩紫骝好。千官暖热李令闲,百马生狞望云老。
望云骓,尔之种类世世奇。当时项王乘尔祖,
分配英豪称霸主。尔身今日逢圣人,从幸巴渝归入秦。
功成事遂身退天之道,何必随群逐队到死蹋红尘。
望云骓,用与不用各有时,尔勿悲。 -
《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骠国乐》
骠之乐器头象驼,音声不合十二和。促舞跳趫筋节硬,
繁辞变乱名字讹。千弹万唱皆咽咽,左旋右转空傞傞。
俯地呼天终不会,曲成调变当如何。德宗深意在柔远,
笙镛不御停娇娥。史馆书为朝贡传,太常编入鞮靺科。
古时陶尧作天子,逊遁亲听康衢歌。又遣遒人持木铎,
遍采讴谣天下过。万人有意皆洞达,四岳不敢施烦苛。
尽令区中击壤块,燕及海外覃恩波。秦霸周衰古官废,
下堙上塞王道颇。共矜异俗同声教,不念齐民方荐瘥。
传称鱼鳖亦咸若,苟能效此诚足多。借如牛马未蒙泽,
岂在抱瓮滋鼋鼍。教化从来有源委,必将泳海先泳河。
是非倒置自古有,骠兮骠兮谁尔诃。 -
《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华原磬》
泗滨浮石裁为磬,古乐疏音少人听。工师小贱牙旷稀,
不辨邪声嫌雅正。正声不屈古调高,钟律参差管弦病。
铿金戛瑟徒相杂,投玉敲冰杳然零。华原软石易追琢,
高下随人无雅郑。弃旧美新由乐胥,自此黄钟不能竞。
玄宗爱乐爱新乐,梨园弟子承恩横。霓裳才彻胡骑来,
云门未得蒙亲定。我藏古磬藏在心,有时激作南风咏。
伯夔曾抚野兽驯,仲尼暂叩春雷盛。何时得向笋簴悬,
为君一吼君心醒。愿君每听念封疆,不遣豺狼剿人命。 -
《庙之神》
我马烦兮释我车,神之庙兮山之阿。予一拜而一祝,
祝予心之无涯。涕汍澜而零落,神寂默而无哗。神兮神兮,
奈神之寂默而不言何。复再拜而再祝,鼓吾腹兮歌吾歌。
歌曰:今耶,古耶,有耶,无耶。福不自神耶,
神不福人耶。巫尔惑耶,稔而诛耶。谒不得耶,
终不可谒耶。返吾驾而遵吾道,庙之木兮山之花。